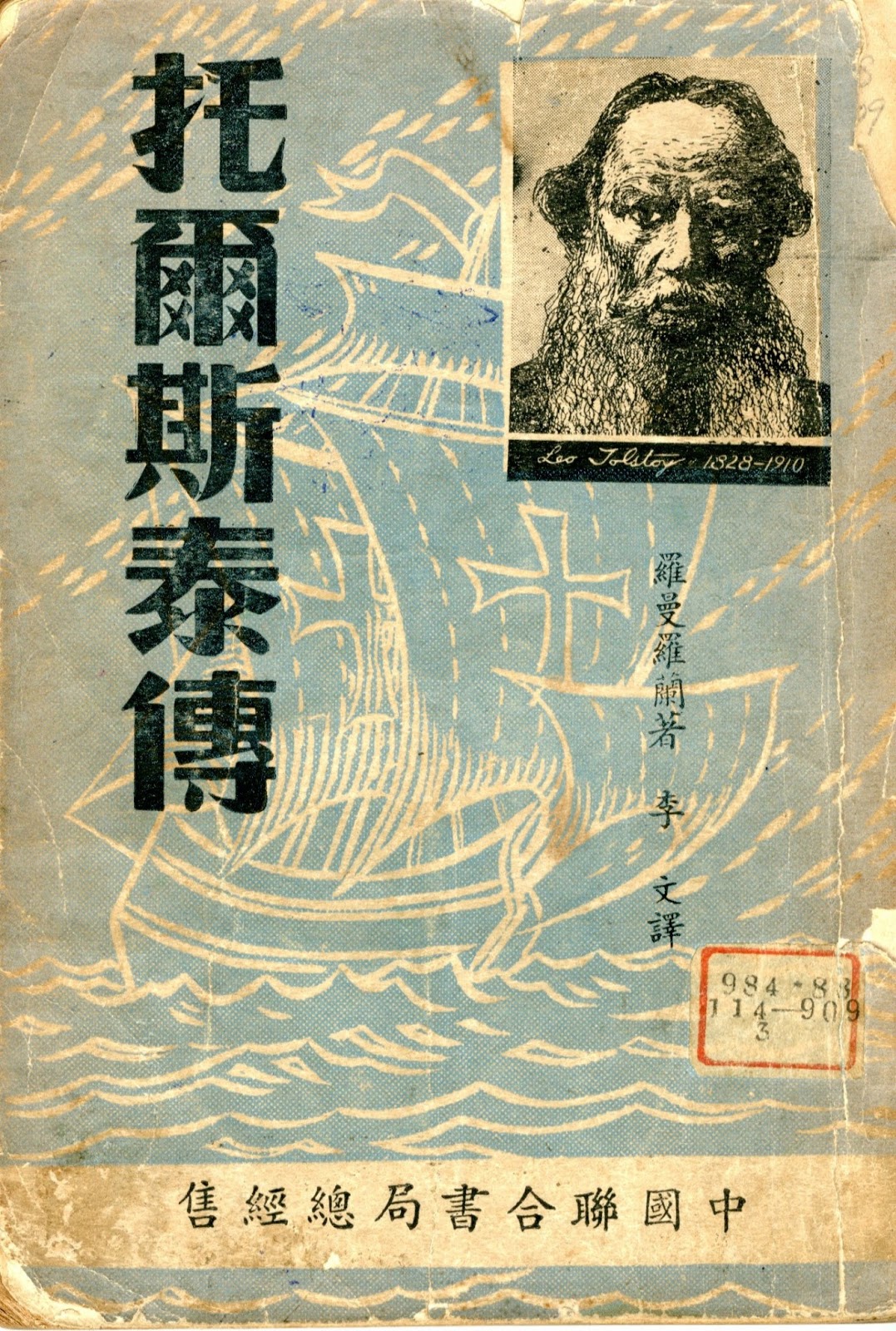|
| 1964新興書局版本,譯者未署名 |
這三本書雖書名不同,卻是同一個譯本,即李青崖(1886-1969)翻譯的《啟示錄的四騎士》(The Four Horsemen of the Apocalypse) ,原作者為伊巴涅茲(Vicente Blasco Ibáñez),20世紀西班牙小說家。原文是西班牙文,李青崖根據法文譯本翻譯。出過兩版,第一版是1929年上海北新書局的版本,第二版是1936年上海商務的版本,台灣出版的這三種版本都是1936年的第二版。兩版差距甚大,譯者在商務版的譯序中詳細說明自己翻譯觀念的轉變:
「那時候(初譯時)對於譯書正主張逐字對譯,並且主張在可能範圍之內,務求譯文的字句的位置構造,應和原文的字句的位置構造相近,以為如此纔可以使讀者領略原書的風格....」
但後來改變看法,發現:
 |
| 1958新興書局版本,譯者未署名 |
「要想把漢文的這兩種組織(心理上和文法上的)同時都和法文的,用一樣的形式並列出來,當然是無法可想的,或者竟可以說是不必想這種可笑的方法。所以初譯本那種主張不變原文風格的譯法,每每遷就文法上的近似的並列式組織,而丟開心理那一層不談。」意思就是以前的譯法只求形似,而忽略讀者的心理;後來則盡可能求明白曉暢而不再妄求形式上的對應。
李青崖在這篇譯序中還比較了自己兩種譯本的幾個例子,非常有趣。如初譯:
「身在那受著海波搖蕩的小輪船中的舒爾,正朝著那郵船仰視...」
再譯版本改為:
「舒爾跳上了一隻被海波動盪的小輪船,抬頭再向那郵船仰視...」
 |
| 1962台灣商務版本 |
李青崖於1969年過世,台灣商務版本1962年出版時,依照戒嚴法,李青崖屬陷匪文人,不能出現名字。不知是否因為這個原因,商務封面上譯者名字作「李清厓」,版權頁寫「李青厓」,都不全對,其實清應作青,厓應作崖。
李青崖在台灣流通的譯本不少,除本書外,還有莫泊桑的多本小說及大仲馬的《三個火槍手》等。李青厓在文革期間過世,《三個火槍手》為其遺作。
李青崖原作
|
台灣流通版本
|
霍多父子集(1929,上海:北新)
|
啟明編譯所(1958),霍多父子集,台北:啟明
|
遺產集(1929,上海:北新)
|
葉娟雯(1973),遺產,台南:東海
|
莫泊桑短篇小說集(1935,上海:商務)
|
啟明編譯所(1958),拔荔士夫人集,台北:啟明
|
溫泉(1955,上海:新文藝)
|
未署名(1966),溫泉,台北:宏業
|
溫泉(1955,上海:新文藝)
|
梁駒(1980),溫泉鄉之戀,台北:志文
|
俊友(1955,上海:新文藝)
|
未署名(1966),俊友,台北:宏業
|
三個火槍手(1978,上海:上海譯文)
|
許智仁(1986),三劍客,台北:志文
|